我的第一张世界地图,压在我家饭桌的玻璃板下面。我总是盯着最大的那块国土,它是淡黄的,名字叫“苏联”,然后会注意到三条河的名字:叶尼塞河、鄂毕河、勒拿河。
它们都是南北走向,从北冰洋往下,扭着拐着,用一种近乎菜谱上说的“改刀”的方式切开淡黄色的大陆,越往南方,就越发分岔、变成细细的末梢。一个人平躺着,通常要比他站直了的时候看起来更高(长)一些,正因此,我觉得这些南北向、带大拐弯的河流,长度实际上都和长江不相上下,也许还略胜一筹。
过了好多年月,我在一篇小说里,读到了对三大河之一——叶尼塞河的描述。作者坐一架小飞机飞往他在西伯利亚的故乡,机上的座位都被各种贩夫走卒、各种乡下人、各种酒鬼和目不识丁的农妇一抢而光,他,一个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进修回来的知识分子,只好站在机舱里。
但他立马发现了站着的好处:可以透过舷窗,将叶尼塞河中游的美景一览无遗。
“我是在山区出生的人,”他写道,“从不曾知道在叶尼塞河中部地带一望无垠伸展着布满沼泽的低地,到处是稀疏落寞的林带、汩汩翻动的泽地,其中还夹杂着黄色的沼泽草地。飞机左翼下方,湖泊水道星罗棋布、纵横交错,波光涟影里野鸭子聚集成群,那白色的星星点点是天鹅和海鸥的身影,相映成趣的是右翼下方那一溜崖岸陡壁,红色的航标像一只红色的秋沙鸭迎面疾驰而来,崖岸上空褐色的悬岩或是折断的山石低垂着,树木顺着石缝枝丫纠结地往上生长,其中有浮着黄沫的合欢树、忍冬、卫矛和树叶发白的合叶子。有一棵树爬上高处后,就在那里神气十足地舒展开了它的树枝。”
文章太长,如果要引,值得一直引用到五千字、一万字、两万字……直到这篇题为《达姆卡》的小说结束。稠密的语言,物象庞杂而分毫不乱,句词每抵达一个角落,都像一条河来到尽头那样既细致入微,又磅礴大气。相比无人机轻松输出的影像,小说里的画面源于作家和译者的精耕,精细而真实到了有如从那地里生长出来的地步:沙滩的浅水处“栖满”了海鸥;河床上有许多仿佛“经过水雷爆炸”的坑,河水到坑中就打起了急旋,到陡急拐弯处,就像“耙过似的起了皱褶”;沼泽间的草地是“低湿”的,分割一块块草地的支流,“汞液般地沉滞”,逐渐消失在前方的林间。
我就是这样,认识了苏联作家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,认识了他的《鱼王》(《达姆卡》是《鱼王》中的一篇),认识了叶尼塞河和西伯利亚,当然也记住了《鱼王》的主要译者——夏仲翼先生的名字。

阿斯塔菲耶夫,今年的,是他的百年诞辰。在他的故乡——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,有一座根据他小说里的描述铸造的雕塑:一条大鲟鱼。它被安置在一座山上,山下就是叶尼塞河,仔细看,鲟鱼的背上不仅有细鳞,而且还有被鱼钩扎伤的痕迹。在书中,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二战前后,叶尼塞河上动魄惊魂的偷猎活动:河岸边的农民,那些缺少教养、焦躁而狂傲的北方俄国人,开着机动船只用鱼叉、用排钩捕鱼,同时与巡河的稽查队“斗智斗勇”,逃避着后者的探照灯和日后严酷无情的刑罚。
在同书名的《鱼王》这一篇里,作家则写了一条受伤的大鲟鱼,不屈于人类的虐待,身带许多鱼钩游向大海的壮烈故事。鱼王塑像的嘴须冲着前方,在下面,叶尼塞河的河边,就是作家的故乡奥夫斯扬卡,而鱼王的脑袋下方,则摊着一本用橘红色大理石做成的厚厚的书。
生命构成一张严密的网
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被译介成中文的很有限,而《鱼王》的光芒则过于耀眼。实际上,这位作家很高产。1958年,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雪在融化》,讲述集体农庄被改造的故事。那年他成为苏联作家联盟的一员,名震全国,《通行证》《星坠》等小说都大受欢迎。1962年,他搬到彼尔姆市,继续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,5年后,他把构思了很久的长篇《牧童与牧女》付梓,但遭到审查机构的干预,他不得不删掉了一部分“敏感”内容。
又过了十年,阿斯塔菲耶夫荣获国家奖,正是这一激励,促使他完成了《鱼王》。在书中,作家将他半生的乡土情怀,以精雕细刻之功倾吐而出:他人生的头十几年,都在北极圈边缘度过,他同跟他同岁的另一位苏联名作家——尤里•邦达列夫一样,都生于1924年,这代俄国人最为悲惨:30年代的饥馑,40年代的战争,50年代的思想和表达禁锢,统统赶上了;而到了六七十年代,成名的阿斯塔菲耶夫,又痛心地看到家乡的水土被机械化生产和过度捕捞弄得精疲力竭。
《鱼王》里人物众多,但位于中心的是偷猎人——有名有姓的并不多,但每个人的故事,他们的语言,他们的动作和情感,都构成了一大片史诗般茂密的景象。我就说一个小例子,在《达姆卡》里,对蚊子咬人这种“小事”,作家是这样写的:
“牛虻向达姆卡袭来,这个地区的牛虻几乎有麻雀般大小,它们的青磷磷的头都成直竖形状,尾部下垂着,身上像斑马般有一条条花纹,嘴上的尖针像铁路上的道钉,你稍一走神,它就立刻会比汽锤还厉害地把针扎进你的背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。牛虻围着小船打转,像军事歼击机那样轰鸣着。额头像出租汽车那样发出磷磷的绿光。”
这是牛虻。之前,阿斯塔菲耶夫还写到一个右臂绑在石膏里的男孩,用左手在玻璃上摁死一只普通蚊子。玻璃的另一边,正淌着雨水,蚊子血的“污流和雨水的清流虽然交叉重叠,却相互冲刷不掉……”
这种画面,靠细致的观察是不足以书写的。阿斯塔菲耶夫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力,他不仅知道人性人心,而且,他能对每一种非人类乃至无生命物体感同身受。在《达姆卡》中,达姆卡打落了一只牛虻,它掉进水里,还想翻身,“一条什么鱼……咂巴一口——这宝贝儿也就无影无踪了!”这画面,这一声“咂巴”,就仿佛作者正在做现场报道——不,就仿佛是那条“什么鱼”在直播它的捕猎行动,在传达这只猎物的口感。
人捕鱼,但人不仅和鱼一样,也在拼命地讨生活,就连一只贪得无厌的蚊子体内都流有人自己的血。生命构成一张严密的网,一个节点以追捕、吞咽、消灭另一个节点的方式来与它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苦难与感恩
阿斯塔菲耶夫曾久历生命从身边丧失。他曾有过三个姐姐,全都夭折;他1岁的时候,家产都被抄了,父亲被判了一个叫做“蓄意破坏国家财产”的罪名,送进了劳改营。到了1931年,他7岁,他的母亲去劳改营看丈夫,在路上搭乘了囚犯坐的船,结果船翻了,她的头发被卡在了木栏杆里,没法爬出来,就这么淹死了。阿斯塔菲耶夫被外公外婆接走,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。然后他的父亲被释放回来,并且再婚,他带着儿子去了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。但父亲很快就病了。继母把阿斯塔菲耶夫扔到街上,他流浪过,然后进了孤儿院,然后又流浪。
这就是他童年的梗概。可阿斯塔菲耶夫日后却说,我记得我孤儿生涯中每一次真正的快乐,我不能忘记它们,上帝最难以容忍的罪行就是忘恩负义,而我,从幼年时起,一种感恩的心情就卡在了我的身上。整本《鱼王》,就是献给叶尼塞河,和河边日渐破落的小镇的,那些野蛮而顽强的人们充满了他的记忆,成为他写作的素材。其中有一篇《鲍加尼达村的鱼汤》,写了村里用大锅煮水熬鱼的时刻,每到这时,村里的小孩——都是一些不知道父亲是谁的“野种”——就欢闹起来。
他们来到岸边,帮着渔民卸下鲜鱼,帮大人分拣和处理,把鱼肉切成小块。他们帮着拿葱、拿盐、拿花椒、拿月桂片,拿各种调料,帮着清洗锅子、拿厨具,当汤刚刚开锅时,他们抢着去品尝味道咸淡。火苗从劈柴中熊熊跃起,鱼汤的颜色由清而浊,蕴蓄着炽热的力量:
“鱼油先只有五戈比银币那么大,后来变得有金卢布那么大了。最后,汤面上的鱼油竟像覆盖了一层熔金。在锅里甚至有什么东西清脆地响了起来,就好像是熔化的金粒滚动着叮叮当当地掉到了这口大铁锅的底部。聂利玛鱼肥大的鱼尾率先冒了出来,带着鱼翅的白鲑翻上翻下,但很快被煮得身翅异处,蜷腹曲背、懒洋洋地张着嘴巴的折乐鱼随势而上,又急转直下,尖尖的鲟鱼头浮出汤的表面,滴溜溜地打转。好一场鱼儿的环圈舞……”
我在读这段文字时不停地咽唾沫。这真的只是一段繁丽形象的文字而已?单靠殚精竭虑的修辞是达不到效果的。如今,很多店都在拿“小时候的味道”“妈妈做的饭”吸引顾客,可我竟觉得,自己记忆最深,一提起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在嘴里泛起滋味的,恰恰是一碗我压根就没有舔过一口的鱼汤。
对,泛泛地讲,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也是爱的力量。
“鲍加尼达”这个中译村名,我相信,翻译家都是动过一番脑筋的——一个“鲍”字就带着鱼的味道。故事中,围绕在一大锅鱼汤周围的孩子中,有两个在村里长大后离去,后来又坐船回到村子的旧址。他们看到,河水已经像舌头一样,把河岸一带完全舔平,灌木丛、茅草和针苔将河岸与冻土带完全连在了一起,村舍彻底坍塌,没有传递出任何有人生活过的气息。这时他们发现,自己只能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刻了,而不好的事情一件都想不起来,就仿佛他们要用某种咒语召唤出那些不知所踪的故人,一起来复活他们曾经落脚过的地方。
无疑,这位回乡之客,就是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本人。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“此心安处”。这里当初就是风雨飘摇,人们身不由己,朝不保夕。如今白色的炉台依然倔强地挺立在蒿草丛中,那两口熬鱼的大铁锅的碎片,已经长满了锈迹,倒卧在了覆盖了浓霜的草丛里面。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,在船上多次眺望过鲍加尼达后,决心不再怀念。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样一番话:
“生活就是这样。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,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。人被抛到哪里,就在那里生根。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,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?”
河流既是拯救者,又是毁灭者
阿斯塔菲耶夫在二战刚结束就结婚了,1947年他有了一个女儿,但只活了6个月,为此她太太埋怨说,他想要靠写作谋生,只能熬穷。严酷的生活在继续,作家倒也顽强,之后三年又生了一男一女。据说他还有私生女。他经常离家出走,尽管每次都会回来。1958年后,他有了名气和地位,然而他没有像作家联盟的其他地方作家一样,落户莫斯科,而是继续待在偏远的外省。
1960年代后半期,苏联经济持续下滑,阿斯塔菲耶夫要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,他多次搬家,而他太太对他放弃定居莫斯科的机会始终耿耿于怀。经过了战后20多年的工业化、机械化建设,叶尼塞河水系遭到了巨大污染,加上过量捕捞和偷猎,到1970年,可捕捞的鱼量比当年锐减了四成。自然环境的恶化,与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活境况发生着共振。
他在一篇小说中写:
“鱼会哭吗?谁知道呢?它们生活在水里,它们就是要哭也无法让我们看到眼泪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它们不会抽泣。它们要是能抽泣的话,叶尼塞河上上下下,甚至所有的大河大海,都会发出回响。”
如果鱼的哭泣能唤起大河的响应,那么,一个被“计划经济”赶来赶去的乡村居民,他的哭泣能震撼莫斯科吗?也许他们的眼泪还没流出,就被冻在了蒙了雾气的眼眶里面吧。
完成《鱼王》时,这位荣誉加身的大作家,其实已经经历过多次破产的危机。他能做的就是坚持写作和发表。《鱼王》包含的各篇小说,从1973年起就在杂志上发表,最终在1976年结集成书出版。可出版时他却住院了。因为他发现,审查机构再度伸手干预,杂志编辑擅自篡改了他的小说。他失望透顶,这是他从心窝里掏给家乡的文字,竟被如此糟蹋。他再也不想看那本书了,当书再版时,他也无心提出要求去修补。
直到1990年,他才找回了当年遭到涂改的原稿,纸张早就泛黄了。他珍视的另一部作品《牧童与牧女》的原稿也找回来了。两本小说都得以原貌重新出版。在我读小说的日子里,《鱼王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盛筵,叶尼塞河、鄂毕河、勒拿河——我对着世界政区图久久想象这些河流两岸的样子,大概水土丰美,草长莺飞,然而《鱼王》揭示了真相:西伯利亚,如此寒冷的地带,河边上竟会有那么庞大的飞舞的蚊群和苍蝇,他们是鱼的美食,却是捕鱼人的死对头。河流养育了人、鱼和虫子,河流既是拯救者,又是毁灭者,它养活了捕鱼人,又随时准备惩罚他们。它是生命之河,也是死神之水;玻璃的一面淌下雨的清流,另一边滚动着死蚊子的浊血。
他的家乡奥夫斯扬卡,现在也是旅游胜地。阿斯塔菲耶夫把自己最后十多年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。每年生日时,都赶上气候最好的季节,他就喜欢来到针叶林里一些无人知道的地方,或者坐在家中的火炉边;到了晚上,他来到叶尼塞河边,坐在一根圆木上——那是他在一张著名的河边照片里的形象,他经历过的日子化为斑点布满了他的脸。
邮件依然可以找到他。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刊和稿件,那都是各地的作者给他寄来,请他写序写评论的。他的名气太大,深受爱戴;他也尽量帮助那些人。可是这无法带给他多少满足感。和另一位苏联老作家瓦连京·拉斯普京一样,阿斯塔菲耶夫也深深体会到,有文化、有才华的人,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越来越不被人需要。按说,写作是和所有人同在的方式,可阿斯塔菲耶夫说,写作的人,只能与自己为伴。
好在还有河流。河流从来不是人类的对立面,而是一个永远的陪伴者,无论它是好是坏,你必须接受他的所有优点,也忍受所有的危害。
奥夫扬斯卡属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,在那里的剧院广场上有一组喷泉雕像,名叫“西伯利亚河流”。这是一组人物群雕,与鲍加尼达村的居民结构相反,这些雕像大部分是女性,她们分别站在一道台阶的两侧,象征着众多的河流;而在台阶中间却是一个男性,他须发茂密,右手平举,手掌上托着一艘捕鱼船。

《鱼王》
[俄]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理想国 2017年4月版

《树号》
[俄]维克多·阿斯塔菲耶夫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·理想国 2017年4月版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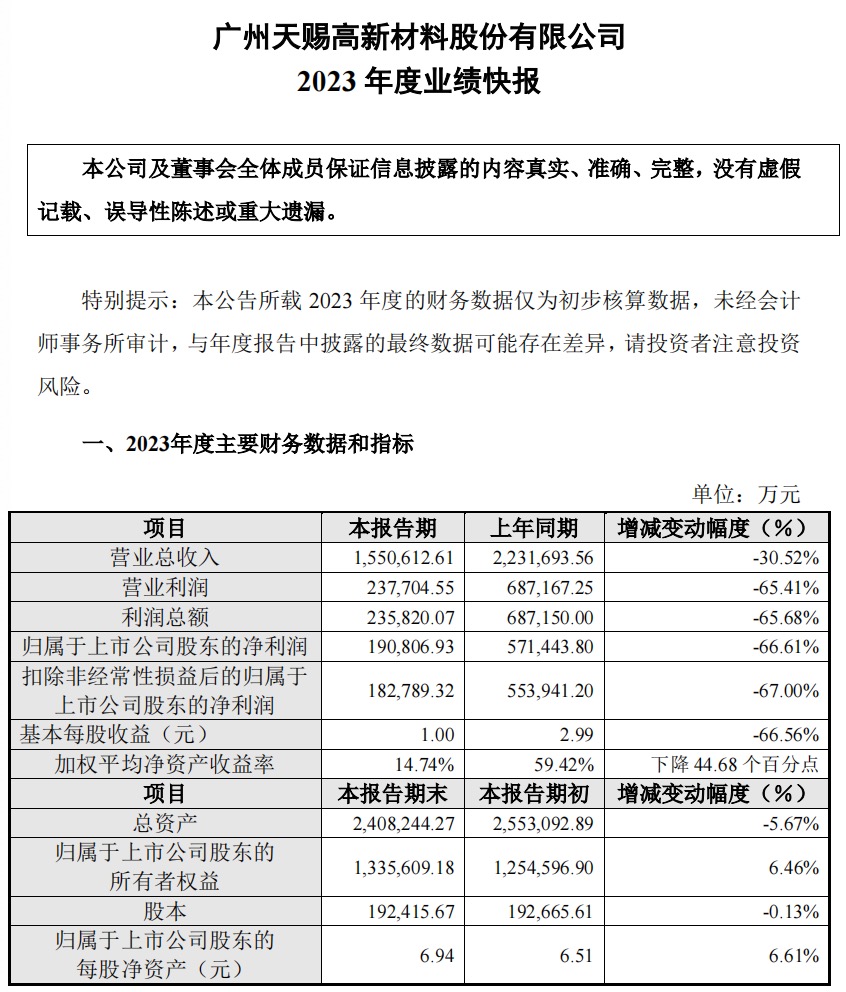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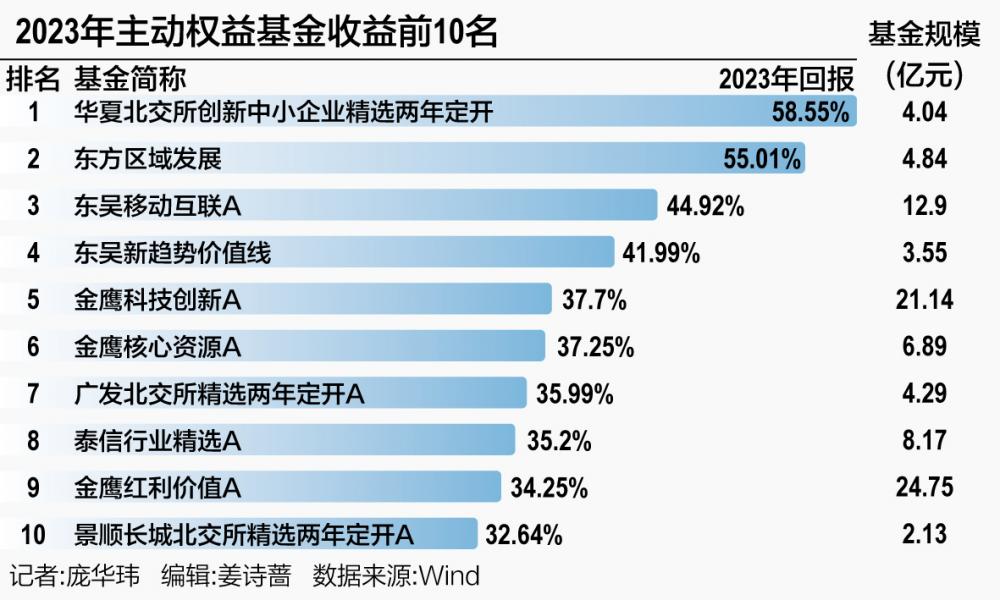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暂无评论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