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23日,经过一年半的装修,“最接近上世纪30年代原貌”的兰新大剧院再次开门迎客。同一天,相距不远的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。
似乎是某种巧合——87岁的陈刚与这两个文化地标相互见证——1959年,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在蓝欣大剧院首演,盛况空;1972年,《红色小提琴》《金色炉石》系列在文化广场首演,遍地黄金。
似乎不仅仅是巧合——也是在这个金秋,87岁的陈刚出版了他的新书《青春岁月》,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上海百年文化的包容、开放、进取,向流淌不息的“上海声音”致敬。
■记者夏斌
陈刚
1935年生于上海,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作者之一,创作了《红色小提琴》系列和交响诗《爱情的悲哀》。曾是第九届、第十届政协委员,2017年被中国文联、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“终身成就音乐家”称号。
泪流满面的梁祝
2022年9月21日,谐音“我爱你”的日子,87岁的陈刚收到了97岁的列车员曹鹏的一封长信。
在信中,曹鹏回忆了他第一次在莫斯科指挥《梁祝》演出时的情景:
“独奏家告诉我,中国的五声音阶很难弹,于是他和钢琴伴奏练了三个月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还有一段大提琴独奏,用滑动的手指来表现中戏的韵味,外国朋友并不熟悉。”
曹鹏说他正在组织一场百年纪念音乐会。三年后,这场“百年音乐会”将再次演奏《梁祝》,“为我一生的音乐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”。
解放周末:你和何合作创作《梁祝》的时候才24岁。据说这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今一个音符都没变,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陈刚:《朱良》一诞生就完蛋了,不需要任何修改。它融合了交响音乐的宏大叙事和中国戏曲独特的表现手法,歌颂了人间永恒的爱情和不朽的亲情。这是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交响音乐,也是我和何送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一份小礼物。
解放周末:《梁祝》的鲜明特色在哪里?
陈刚:传统的协奏曲一般由三个乐章组成,但《梁祝》根据自身音乐发展的需要,被一气呵成地写成了单乐章协奏曲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首演后,有评论认为不像协奏曲。但是我觉得,一章能写清楚的东西,为什么一定要用三章来表达呢?协奏曲的本质是协奏曲,而不是乐章的数量。之所以采用单乐章结构,是因为这样可以更集中地表现朱良的爱情主题,表现爱情和反抗两条线索的交织,人性的冲突和张扬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意。
另外,常规的交响乐团是由弦乐、管乐和打击乐器组成的。打击乐有锣鼓,但从来没有中国班固。但是,当我们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表达“天天哭不应,哭地不灵”的悲痛时,就需要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。这个时候,几乎所有的西方乐器都失灵了,无能为力。只有中国鼓能击碎你的灵魂,让你心碎。因此,我们大胆打破常规,推陈出新,在交响乐团中加入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班固。从此,全世界所有的交响乐团在演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,都必须加上这种中国乐器。
几百年前,中国曾经为全世界的管弦乐队贡献了一面锣;后来,我们贡献了这个独特的班固。当时,当指挥家曹鹏在苏联首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时,他跑遍了整个莫斯科去寻找这个班固。最后,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格林卡博物馆看到了班固的展览,它就像一件珍宝。
解放周末:1959年5月,《梁祝》在蓝欣大剧院首映。当作品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,你在哪里?
陈刚:在《梁祝》的首映式上,观众被俞丽拿的钢琴余音迷住了,而我却胆怯地躲在舞台后面偷听。当结束时,空看起来像一个浓缩的盘子。我心想:怎么没有半丝反应?没有回音?
不知道过了多久,也许是短暂的,也许是漫长的,掌声突然一波又一波地滚滚而来。每个人都击鼓,击鼓,击鼓,击鼓,击鼓,击鼓,直到俞丽拿不得不从头到尾再演奏一遍整首协奏曲。从我自己的眼泪里望出去,我看到许多听众的眼里也闪烁着泪水。
不会忘记三个“第一”
陈刚年轻的时候没有音乐梦。
因为,学钢琴很不开心。老师很严格。弹钢琴时,他把一个火柴盒放在陈刚的手背上。每次他滑下来,都会砸到手。
比起音乐,陈刚更喜欢文学。他整天躲在被窝里看书。在写《我的志愿》时,他写道:“我不想当大官,也不想发财。我只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!”
但是,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改变。1949年,这个凶悍的14岁少年抛开文学梦想,报名参军。虽然,兜兜转转之后,他又被送回了乐坛——看似回到了原点,其实他已经长大了。
解放周末: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问世,新中国有了一部可以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交响乐。在这成功的“第一步”背后,你付出了哪些努力?
陈刚:一方面,我有“家庭秘方”。因为我出生在音乐世家,所以被我的曝光滋养。父亲在审美情趣和乐理基础上为我做了铺垫。
另一方面,我较早步入社会。1949年上海解放时,我刚初中毕业,立志从军,投身革命。于是,我用橡皮擦把初中毕业证年龄一栏里“14岁”的“4”擦掉,改成“8”,抹上一点酱油,弄得有点模糊,大胆地装成18岁,一路唱着《国际歌》报考华东军政大学。
一年后,我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一所机要干部学校。但是体检的时候被告知眼睛近视,要回去。很幸运,我的指导老师说:“你不是学过钢琴吗?我们会训练你,去文化集训队。”
培训团队每月支付20元学费,送我去跟马教授学琴。从文化集训队毕业后,我来到一线歌舞团当钢琴演奏员。抗美援朝之际,我试着写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《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》。我有幸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,拿到了5元稿酬。那首歌现在看起来不怎么灵动,但对我的启发很大,埋下了一个小小的,朦胧的作曲想法。
解放周末:这次从军经历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陈刚:这次经历有三个第一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那是第一顿饭。那时候我们都是军人,吃饭的时候带了一个没用的大水桶。我近视,脸色发黄,舀之前闻到一股香味,以为是蛋炒饭。结果我吃了第一口,差点把牙咬掉——原来是小米。上海的孩子没怎么吃过北方的小米,我印象很深。但在此之前,中国很多人吃不到这样的饭。
二是第一首歌。我们在解放区学习了几天。我还记得,大队长和部队队长领着我们唱歌的时候,都是双手握拳,竖起大拇指指点方向。后来在电影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里看到,里面的一个连长也是这么指挥的。这首歌,对我们来说,似乎是一个符号,解放区的天空是一片晴空。
这是第一双鞋。那是我参军后收到的第一双鞋。是山东老奶奶给的。虽然是布鞋,但是比皮鞋更厚更硬。后来我去山东,看到山脊上全是老弱妇孺,很多年轻人已经死在前线了。这双布鞋,是普通人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中国,把孩子送上前线,把生命献给事业的见证。
后来去了很多殿堂级的剧场,有很多艰辛的经历。这三个“第一次”是我人生的起点,这段经历也给我的成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,带给我真诚而坚强的信念,陪伴我走过风风雨雨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,我也始终相信自己的初心是正确的,不变的。
作文是一个“场”
“你好,帕姆!”9月23日,在上海文化广场70周年纪念活动中,陈刚在悉尼与潘寅林[/k0/]进行了一次对话。
白发苍苍,但在陈刚眼里,他仍然是“林中之虎”潘。
1972年,潘寅林登上千人聚集的文化广场,首演了陈刚创作的《红色小提琴》系列。洛杉矶的第一部作品是《金色壁炉》。这一拉,让“金”遍了文化广场,也轰动了整个上海。据说学钢琴的人急剧增加,工厂一年生产了10万把小提琴。在火灾最严重的时候,潘寅林正在过马路,交警看到了他,红灯突然变成了绿灯。
《金灶台》、《苗岭的早晨》、《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》……美妙的琴声凝聚了时代的波澜和人性的渴望,成为特殊时代的一缕阳光。
解放周末:继《梁祝》之后,你为什么选择创作《红小提琴》系列?
陈刚: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人们其实很渴望用音乐来抚慰心灵。当时,潘寅林刚刚升任上海交响乐团首席,但他经常担心演出单调,于是他找到我,希望我能创作一些新的小提琴作品。这个邀请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。我一口气写了八九首小提琴作品,包括最流行的《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》。
解放周末:从《金灶台》到《苗岭的早晨》和《塔什库尔干的阳光》,“红色小提琴”系列听起来很美,热情洋溢,充满希望。
陈刚: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展示着伟大的时代和普通人的内心,就像充满生命力的种子会在土壤中自然地自由而有力地生长,最终成长为灵魂的绿荫。
这是我对“红色”的解读。是花样年华里的一抹朝霞,是蹉跎岁月里的一段激情浪漫,是我们心中的一朵不可战胜的玫瑰。创作“红色小提琴”系列时,我首先想到的是让小提琴这种西方乐器“唱出”中国人的审美要求,以此作为作曲家的责任,表达当时中国人对“阳光”的普遍需求和对生活的希望。
艺术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,但能代代相传的,一定是跨时代的,超现实的。马勒最悲剧的交响曲是在他最快乐的时候创作的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试图在作品中注入生命的光明和热情,描绘人性、亲情和温暖的状态,表现人们对多彩生活复苏的渴望。
我的朋友程乃山曾评价说,“这些特定时代的歌曲,有一个旋律简单如春雨,淡定如菊花,像一个过滤器,把焦虑、不安、怨恨、怀疑过滤掉,留下希望。”
解放周末:除了作曲家,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——上海音乐学院教授,负责培养更多的作曲家。你是怎么教学生的?
陈刚:我教学生的秘诀是“不教”。我觉得作曲家教不了,恐怕艺术家也教不了。你的基本功可以很好,你的技术可以很好,你的作品可以这样那样,但是不像你自己。这样的作品能称为艺术品吗?
我的很多学生都很优秀。我主要是教一点我的审美观念,更重要的是根据每个人独特的创作路径,给他们一些建议,具有自由性和真实性。当然,我也会给我的学生讲一些我的经历和教训。比如要写这类作品,就要同时听一些东西,从大家的作品中吸取营养,充实自己。
我一直认为作文不是一门课,而是一个“场”,一个鲜活的“场”。学生应该处于充分的创造状态,而不是被动的实践状态。
当一些学生在我的班上学习时,他们创作了一首由首无伴奏的大提琴独奏。为了模仿古琴的声音,他把大提琴降低了四度。演出结束后有很多谩骂,但我支持他。因为他不是在玩音频游戏,而是刻意试图将中国古韵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。民族的养料是我们创作的源泉,江河应该流向大海,流向世界,流向现代。
散发上海文化的光芒
前不久,陈刚出了一本新书《盛开的岁月》。这是他的第五部散文集,讲述了他的个人史和家族史,也是上海音乐史和文化史的生动一笔。
新书发布会将在上海图书馆新落成的东馆举行。在发布会上,邀请了几位老朋友:昆曲表演艺术家沈昳丽表演了《惊梦》的片段,电影表演艺术家赵静讲述了她与陈刚的过往,“佐罗”童訾荣深情地朗诵了书中的片段。
更多的老朋友,更多的上海风雅,都在陈刚的笔下,触手可及。
陈刚说,从一个“音乐人”到一个“作家”,永远不变的是上海的声音,是上海的故事。他希望自己能用音符和文字书写这座伟大的城市,让她永远以最新最美的姿态屹立于世界。
解放周末:为什么推出这样一本新书?
陈刚:去年,《义勇军三月》记录的“EMI大楼”正式挂牌。当我踏进“小红楼”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我恰好和义勇军的马奇同龄。当时我们正在一起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国际歌》的《前进!去吧!去吧!进入!”是的。
去“小红屋”二楼展厅,更是倍感亲切。以前来我家的叔叔阿姨们,都在墙上对我笑——周璇、姚莉、白光等。他们演唱了《玫瑰玫瑰》、《玫瑰》、《我爱你》、《苏州河畔》、《上海之夜》和《永远的微笑》等著名歌曲。黎锦光先生还亲自告诉我如何写夜来香。
作家白先勇曾告诉我,上海对他来说有着巨大的魔力和魅力。他没想到,童年时路过百乐门时看到的上海女人的体态,会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,以至于成为他两部短篇小说的原型。
我觉得上海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,生活中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,朋友们有那么多难忘的故事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上海的百年激越与优雅,应该记录下来,传承下去,再不讲述就会被遗忘。所以我要求自己转换角色,写这些故事,这也是童年的文学梦。
解放周末:在你的心目中,有哪些老朋友和朋友特别值得你去书写和缅怀?
陈刚:我对小提琴手斯特恩印象深刻。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见过他两次。从他身上,我能真切地感受到,一个艺人就是一个普通人,一个简单的人,比普通人更普通,比简单人更简单。真正的艺术家的眼睛是透明的,天真无邪的,但是他一丝不苟,在艺术上追求完美,我们想成为这样的艺术家,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艺术家。
今年5月,秦怡去世。她95岁的时候,我在墨尔本和她一起弹琴,朗诵了《陆妈妈的独白》。我们一起排练,一起表演,每次钢琴慢慢落下,她的眼泪总会掉下来。她是电影明星,当年剧坛“四大名人”之一,但同时,她也是一个普通的“亭子间大嫂”,什么都买得起,什么都放得下。她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一想到她,我就想到了崇高与平凡,美丽与隐忍。
解放周末:如果让你“写”自己,你会从哪里开始?
陈刚:我觉得艺术家,艺术家,艺术才是家。作为中国的艺术家,我的家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。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,我的家在世界文化的海洋里。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艺术家,我的家是上海的文化。
我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上海,爱上海的摩天大楼和街道,爱黄浦江的汽笛,爱江海的大钟。
在艺术上,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、第一个音乐学院、第一个艺术学校……几乎所有的“第一”都是从上海开始的。他们出生在上海并非偶然。
上海的城市文化是什么?记得茅盾在《子夜》里用了三个词——“光”“热”“能量”。他说,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“光”、“热”、“能”,这是现代文明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。海派文化有三个特点:都市情怀,中西合璧,雅俗共赏。由此,上海的文化创意不仅奔放空且充满思想,而且大众化、接地气、与市场接轨、与民众接轨。
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些恢复和弘扬海派文化的事情,试图寻找海派文化的音乐形象和代言人。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内心的声音,找到人性的声音,找到上海的味道,找到城市的灵魂,从而放射出上海文化的光芒。
来源:解放日报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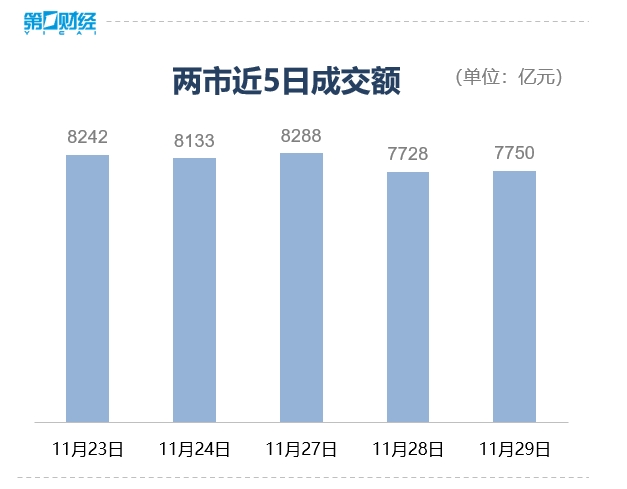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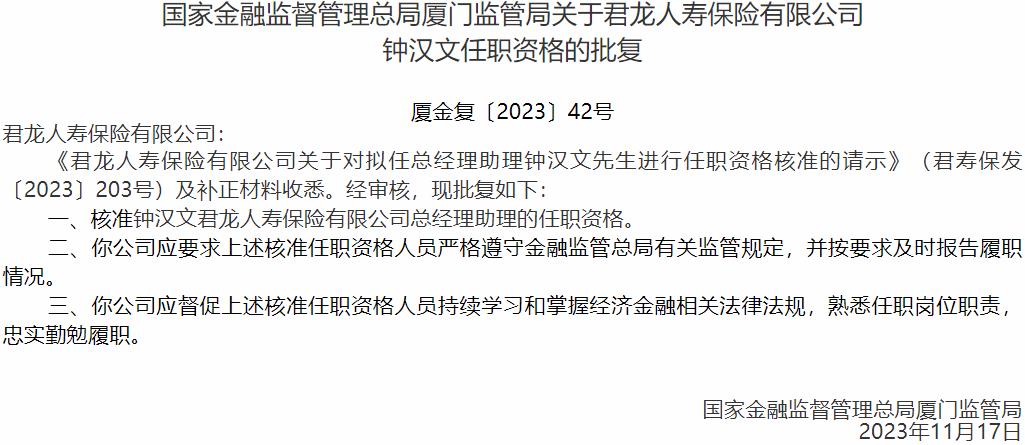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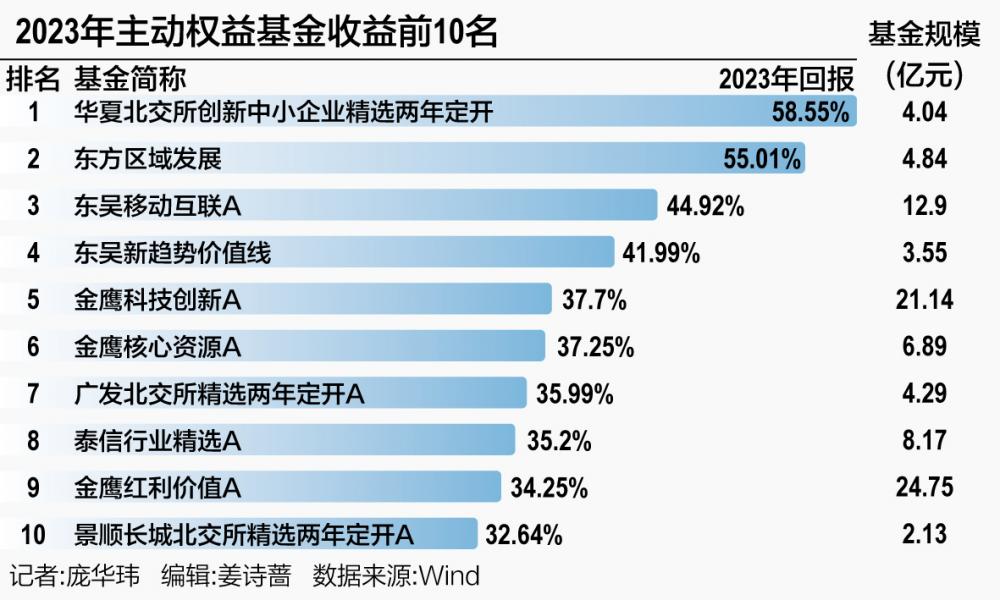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暂无评论内容